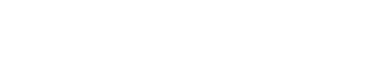今年年初,我到济南参加会议,住在翰林大酒店。站立窗前北望,两排法桐映入眼帘。风吹叶落,往昔那个熟悉的山师校园又勾起了我的回忆。于是,我卸下一路旅途的疲惫,一个人走出酒店,东拐北折,就进入这年少时求知的地方。
进入校园,首先要到2号宿舍楼。那年大二开学时,我们从荒凉的北校区来到文化气息浓厚的老校区,也就是现在的千佛山校区。此后3年,我们在这个植满绿树和花草的园子里上下求索、探索新知。2号楼343宿舍,是我们7位同学共同的家。当时的我尤爱宿舍窗后的核桃树。那大片大片的核桃叶叶交通,长得尤其迷人。暑假开学时,正是绿叶婆娑满枝的时候,我常常临窗而立,静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投下点点斑驳的光影。只可惜现在是冬季,核桃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那时曾经熟悉的人们也都已各奔东西,不禁让人生发出物是人非的慨叹。
漫步校园,不知不觉来到了教学三楼。印象中二楼原先是中文系领导办公和师生上课的地方。看到一间间教室,我不禁联想到当年自己上课的情景,在脑海中思索着在这个同样的位置,自己曾经上过什么课,这门课程由哪位老师教授。时光如梭,一晃30年过去,想象重叠、影像交织,各位先生的音容笑貌却如在眼前。
回到一楼,我挨个查看走廊上的标牌和文字,为文学院这些年以来取得的进步和发展感到由衷的自豪。此时,“吱呀”一声,邻近的办公室门打开,一位精神焕发的男士走出来。四目相对间,我开始进行一番自我介绍。校友、系友,我甚至把同班留校的两位教授的大名也搬了出来。我问对方尊姓,始知站在面前的,竟是李宗刚教授。李教授不是我的授业老师,但在我有限的认知里,他的五四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教育研究,以及由此而体现出的人格魅力与学术精神,让我油然而生敬意。
寒暄过后,李教授回办公室“继续革命”。我忽然想起,临来时捎带的一本《山师学者视阈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编选者就是李教授,何不让李教授签名留念?念头一起,我不禁喜上眉梢,索性回住所取书。在这个日落黄昏的时刻,谁也不知道这个年过半百的外地人究竟为何这般行色匆匆。只有我明白,作者的签名对于读者的意义,不只是书写几个符号,更是一种精神的贴近与引领。
带着这种意念,我兴致勃勃来到李教授办公室。我轻轻叩响了门,李教授开门见我,颇感意外。我急忙说明签名之请,并把书奉上。他见到书颇感惊喜,抚摸着书封,仔细询问书哪里来,价格多少。李教授一边夸赞我爱书向学,一边慨叹此书颇有影响,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立刻在一沓红笔圈点的稿子边找签字笔,竟遍寻不见。
李教授邀请我到办公室。我恭敬从命,跟着李教授西走北拐,到了另一间办公室。此屋面积不大,南北两面是书橱,中间是办公桌,上有一台电脑,其余就是一摞摞书和一沓厚厚的文稿,最上页画满了红线,还有红圈点。他打开前面书橱,左右浏览,继而又俯身查看下层书柜,上下搜寻,终于觅得3本书——《穿越时空的鲁迅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发展纪略》《民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研究》。看着李教授热情忙碌找书的样子,我非常感动,感谢他视我初识即为故人。他一本书一本书打开,一个字一个字郑重地为我留言签名。大学教授与中学教师、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学语文、山师学长与地方学弟,我们就这样通过简短的几句留言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语文教学不正是需要这种大学和中学、教授和一线教师、学术和知识、素养与能力的融合吗?打通壁垒、加强交流、实现贯通,不正是我们做好语文教学的必由之路吗?
最后,我提出与李教授合影留念的想法,他爽快答应。为方便起见,我打算自己用手机拍照。李教授郑重地说可以找人帮忙,说话间就跑到另一办公室喊人。巧合的是,来人竟是韩品玉老师。韩老师是次日会议的主角,正忙着准备会议。没想到我以偶遇的方式向韩老师提前报到。韩老师对我的出现也有些意外,“明春”,他一眼认出我并亲切地喊出了名字。在李教授的办公室里,我们3人,在手机灯光的闪烁中留下了珍贵的纪念。
天黑了,一楼只有李教授和韩老师的办公室还在亮着灯。一个忙着研究学问,一个忙着准备会议。在校园里,在教学楼里,我不过是闲情偶寄,走走停停,消磨一下时间。带了一本书,竟幸遇书的编选者;喊人拍照,竟喊来了会议的主角。天机赐巧,母校赐缘,有勤勉师长可学,有精美书籍相伴,我是如此幸运。
吕明春,中文系1990级本科生,现为定陶一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