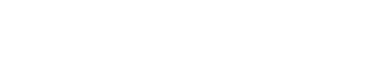回顾自己的人生特别是教学历程,最难忘的是开设英汉翻译课(简称:翻译课)和编写并开设英国文学选读和美国为办学选读的经历了。后面两门课程的开设均为自编教材,若干年后才有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教研社出版的吴伟仁编《英国文学史级选读》等教材。而记忆中较为深刻的是开设英汉翻译的第一堂课。
站在山东师范大学的讲台上时,我的教案边角还沾着北大的梧桐叶香。新学期第一堂课,望着台下三十多张年轻的面庞,忽然意识到自己已从翻译学的求道者,变成了传灯人。从学生到教师的身份转变,让我深刻体会到“教书育人”这四个字的分量。不过,我的教法是深受张谷若先生影响,有他的烙印或影子的。我的翻译课并没有从课本开始,而是从翻译的本质讲起。我告诉学生们:“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文化的传递,更是文明的摆渡。”这句话不仅是对他们的期望,也是对我自己的鞭策。我希望通过我的课堂,让学生们明白翻译的价值与意义,而不仅仅是掌握一门技能。这门课程,到为研究生开课时,则称“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后来几经改成,最后成为“翻译与文化——近代文学翻译的崛起与影响。”还从头至尾做了Powerpoint课件。
我始终坚持因材施教,发现每个学生的闪光点。我还记得那个腼腆的女学生,她译的作品总带着怯意。迄今,她已经翻译出版了十几部长篇小说,现在仍在课余笔耕不辍。
我常对学生说:“翻译是一项需要耐心和毅力的工作,板凳要坐十年冷。”这句话不仅是对他们的要求,也是我自己的座右铭。无论是翻译《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还是《汤姆叔叔的小屋》,我都精益求精。“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训诫还挂在教研室墙上,77级学生赠的竹雕笔筒已沁出包浆。筒身“春风化雨”的篆刻,见证过无数个与年轻译者推敲词句的寒夜。而今我的青丝已成暮雪,却依然保持着清晨五点备课的习惯。我修订《剑桥大学简史》译稿时,一位研究生问我为何坚持做注。我说,做注主要是为读者扫清理解障碍,也说明译者态度之认真。另外,还顺便介绍了我的老师张谷若先生的英国古典文学译作的特色之一,便是注释之多,令人惊艳。李赋宁先生评价张先生的译作时,就说过:对古典文学的注释本身就是正儿八经的学术研究。
粉笔灰依旧在晨光中纷扬,如无数微小的星火盘旋。我轻抚讲台边缘经年累月的木质纹路,那里沉淀着四十年光阴的故事。当夕阳为教室镀上金边,总能在年轻学子专注的眉眼间,看见未名湖畔那个怀抱译著的青衫少年——文明的薪火就这样在讲台间流转,从青丝到白发,从昨天向明天。
我始终坚信,教育是一项充满智慧与爱的事业。作为教师,我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与使命。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以“师者本色”为指引,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简介:
李自修,1939年生,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曾任英语系主任,全国美国文学学会理事,全国英国文学学会理事,山东省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山东省翻译协会副会长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