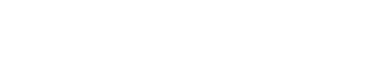在这秋收冬藏之际,我先后收到了两部著作:山东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魏建、李宗刚等编著的《蒋心焕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和李宗刚编选的《朱德发学术手稿选编》(团结出版社2023年版)。这不禁让我回忆起在母校攻读硕士学位时曾经给我深刻影响的两位老师,一位是蒋心焕先生,另一位是朱德发先生。他们是除了我的指导教师田仲济先生之外对我影响较大的两位老师。
《蒋心焕志》是蒋心焕先生人生轨迹和学术成就的描摹与梳理。本书用原始档案、照片、手稿、笔记、日记和现今的访谈、回忆文等,以客观、主观交汇互补的方式,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第二代学者蒋心焕先生的形象及心灵世界得以客观真实又极富感情色彩的呈现。蒋先生是一位学术成就辉煌、散发着人格魅力的新中国培养的一代优秀知识分子。读来令人动容,不禁潸然泪下。
《蒋心焕志》的编写是一项值得称赞的创举。它通过一个人的历史,映射出一代学人、一门学科乃至学派的历史,折射出整个时代的教育史、文化史乃至整个国家翻天覆地的社会变迁,其意义难以估量。而其在文体方面的创新则开了先河,这对于文学和历史的书写均具有启发价值和意义。
《朱德发学术手稿选编》则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的著作,这也是编选者为朱德发先生以及山东师大现当代文学学科树立的一个界碑,是对当下手稿研究热的一次积极回应。编者在《前言》中提出朱先生是“思想者”乃至“思想家”的观点,我觉得很有道理。翻阅其手稿,我们会感到朱先生的字迹正如同他的思路一样清晰。朱先生写论文,往往不打草稿,正所谓烂熟于心、一挥而就。朱先生的手稿虽书写在一格一字的稿纸上,但他却不受格式的拘束,往往连成一脉。我想,他大概不愿因一格一字产生的短暂停顿而妨碍思路流水般的畅达。我们看其手稿中有并不多的修改和润色,则恰好昭示了他的深思熟虑和严谨认真。对于我们而言,真可谓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朱先生的文学研究具有思想解放的特质,在学术研究的许多方面,则是一位引领者。他又异常勤奋,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著述。朱先生堪称一位学术成就卓越的学者,其人其文葆有永恒的影响力。编者撰写的这篇《前言》也写得情理并茂,如读美文,与所选手稿相得益彰。
几年前,著名学者彭定安先生与我交谈时,曾提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朱德发先生为领军人物的“齐鲁学派”。他将青岛大学也涵括其中。我觉得还是命名为“山师学派”更为合宜:青岛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从沿革上看,事实上乃是“山师学派”的分蘖,追根溯源,有田仲济先生和薛绥之先生的筚路蓝缕之功。
三代学人高度自觉的代际传承,是山东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重要特质之一。如果说朱德发先生协助田仲济先生修改《中国抗战文艺史》,蒋心焕先生协助田仲济先生编纂《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散文杂文集》是第二代学人对第一代学人的自觉传承,那么魏建、李宗刚编著的《蒋心焕志》和李宗刚编选的《朱德发学术手稿选编》则是第三代学人对第二代学人的承传。相较之下,传承者的自觉意识更强,承前启后意识也更加鲜明。他们要用朱先生和蒋先生之学术荣光不单照亮自己,而且照亮后学,照亮山东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乃至照亮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
朱先生和蒋先生可以视为山东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人中的“双子星座”。虽说他们是红花和绿叶的关系,两人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有别,但这“红花”和“绿叶”是彼此互动、互相成就的,共同襄举了山东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与壮大。山东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若是缺其一人,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层级与光彩,至少在对第三代学人培养的成绩上要大打折扣。更何况两人有着同等的人格魅力。就人格魅力而言,蒋先生甚至更丰富多彩一些。但朱先生作为五四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与重镇,理性世界更丰富一些。当年,朱先生身居五排房的斗室,将物质空间的逼仄,化作学术空间的辽阔,将人生的困顿转为学术创作的自由,成为鲁迅先生所呼唤的“真的人”。
我以为,朱先生和蒋先生不独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研究这一学海中的“双子星座”,亦是人格中的“双子星座”。他们的为人为文高度和谐统一。这也正是山东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奠基人田仲济先生为这一学科播下的重要品格。
《蒋心焕志》和《朱德发学术手稿选编》这两部书的意义远远超越对其本人的纪念。这两部书的编写、编选与出版使得山东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第二代学人这对“双子星座”显现出在代际传承中不可或缺的历史地位。他们虽然离开了一生为之奉献生命的学科,但他们的学术精神不会消失。
(作者系我校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1979级硕士研究生,现为辽宁省社科院研究员、鲁迅研究专家。)
(本文刊登于《山东师大报》1732期第4版)